
安全国家是指认为其国家生存受到威胁或主权存在受到危险,从而将国家资源主要用于安全而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国家。
生存是安全国家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但是,这样的国家只有在得到支付的情况下才能维持下去,因为“增长而不是枪支”是通往安全的最可靠途径。(Karamat;哈佛大学:2005)
一个安全国家决定了一个食利者国家和一个食利者经济,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
这是国家和社会的“掠夺性占领”。食利者经济是最简单的选择,因为真正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的,民主要求包容、宽容和妥协,这是安全国家所反对的。
Geocomo Luciani和Hazem al Bablawi (The Rentier State: 1987)在《食利者国家》(The Rentier State)一书中对食利者国家的定义是,在阿拉伯的背景下,一个国家从出售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中获得盈余,而不增加经济生产力,也不向公民征税。
这种地位也可以通过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地缘战略位置进行讨价还价来获得,但要注意的是,世界事务的变化可能会影响一个国家的食利者地位,就像巴基斯坦目前目睹的那样,外国经济和军事援助正在减少到涓涓细流。
食利国展示了一种特殊的国家形成路径,这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欧洲的国家形成路径:依赖自然资源或利用地理位置作为地缘战略资产,以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形式吸引大国投资,从而创造出与社会需求脱节、几乎不依赖国内税收的弱国。民主问责制缺乏发展。国家只提供安全、法律和秩序,最不愿意投资于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
在我国,封建食利者阶级仍然是免税的。土地改革并没有像印度许多省份那样,在家庭的基础上规定所有权的限制。结果,尽管进行了几次土地改革,封建领主仍然拥有数千英亩土地,作为不生产的缺席地主。
尽管没有石油或稀有矿产,巴基斯坦是一个食利者国家和经济体。自1947年以来,我们已经变得依赖于我们的地理位置讨价还价,利用我们自己来结盟或摆姿势,以促进大国的地缘战略目标。
在另一个层面上,工人的汇款是另一种形式的食利主义,因为这些收益是在增加国内生产率之外的,其中大部分增加了消费。
房地产行业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尽管它对实际增长的贡献微乎其微。
在塑造民主进程、管理民选政府和边缘化那些被视为对军事统治构成威胁的政府方面,安全国家直接或间接地发挥了关键作用。
67% - 73%的税收来自进口和间接税;个人所得税只占总收入的27%,这表明富人享受的免税待遇与他们获得的巨额收益相比微不足道。
受保护的消费导向是食利者经济的典型特征。投资被转移到产生非生产性租金的领域,如房地产、物业、住房和投机投资。
不充分的土地改革使无地工资和抵债劳工问题得不到解决。由于地主对地方警察、税收和法院、学校、灌溉等国家服务的控制,口袋选区变得根深蒂固。
所有的军事独裁者,涵盖了我们35年的国家生活,扩大和巩固了封建主义,使其成为政治政权的伙伴,在抢椅子的游戏中。
在阿尤布、齐亚和穆沙拉夫的统治下,通过地方政府的实验,将权力下放到基层,目的是为独裁者创造一个选民群体,为他们的统治提供合法性。而不是下放实权,权力更集中于强化封建贵族旨在缩小和削减。
自分治以来,有两个因素对我们所有的国家政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印度的恐惧和对克什米尔的民族统一主义。
我们加入Cento和Seato并不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而是为了在军事上支持我们对抗印度。在独立后的最初几年里,我们被一种恐惧所压倒,害怕作为一个自由国家被一个比我们大五倍的邻国摧毁,这个邻国反对把一个统一的国家分裂成两个。
这导致我们不顾一切地寻求外部帮助,以加强我们的防御能力。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加入了Seato和Cento,表面上是美国领导的遏制苏联领导的“红色威胁”的伙伴,但实际上,我们试图保护自己免受西方对我们生存的任何有害威胁。
国防和军事援助之后,美国、欧洲和布雷顿森林金融机构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财政援助。
据估计,巴基斯坦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了不少于150亿美元的外援,这帮助它成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展示。在齐亚和穆沙拉夫统治的20年里,正是我们在反苏和后来的反恐立场上讨好美国,才使近200亿美元的援助成为表面上的援助,而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
1970年以前的西巴基斯坦和东巴基斯坦关系是一个典型的安全国家和国内食利主义的例子。
在阿尤布、齐亚和穆沙拉夫时期,外部援助提供了350亿美元;韩国在经济形成时期只获得了150亿美元。当外部援助没有用于提高生产率,而是用于食利者保护主义和进口替代时,关键的35年就失去了。
是不是由于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或因素,我们还没有成为一个正常的生产性经济体?安全国家和食利主义在我们的星球上存在吗?为什么一些与我们几乎同时从殖民主义中独立出来的地位相似的经济体表现得更好呢?这些都是需要深刻思考和纠正的问题。
安全国家是指认为其国家生存受到威胁或主权存在受到危险,从而将国家资源主要用于安全而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国家。
生存是安全国家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但是,这样的国家只有在得到支付的情况下才能维持下去,因为“增长而不是枪支”是通往安全的最可靠途径。(Karamat;哈佛大学:2005)
一个安全国家决定了一个食利者国家和一个食利者经济,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
这是国家和社会的“掠夺性占领”。食利者经济是最简单的选择,因为真正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的,民主要求包容、宽容和妥协,这是安全国家所反对的。
Geocomo Luciani和Hazem al Bablawi (The Rentier State: 1987)在《食利者国家》(The Rentier State)一书中对食利者国家的定义是,在阿拉伯的背景下,一个国家从出售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中获得盈余,而不增加经济生产力,也不向公民征税。
这种地位也可以通过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地缘战略位置进行讨价还价来获得,但要注意的是,世界事务的变化可能会影响一个国家的食利者地位,就像巴基斯坦目前目睹的那样,外国经济和军事援助正在减少到涓涓细流。
食利国展示了一种特殊的国家形成路径,这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欧洲的国家形成路径:依赖自然资源或利用地理位置作为地缘战略资产,以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形式吸引大国投资,从而创造出与社会需求脱节、几乎不依赖国内税收的弱国。民主问责制缺乏发展。国家只提供安全、法律和秩序,最不愿意投资于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
在我国,封建食利者阶级仍然是免税的。土地改革并没有像印度许多省份那样,在家庭的基础上规定所有权的限制。结果,尽管进行了几次土地改革,封建领主仍然拥有数千英亩土地,作为不生产的缺席地主。
尽管没有石油或稀有矿产,巴基斯坦是一个食利者国家和经济体。自1947年以来,我们已经变得依赖于我们的地理位置讨价还价,利用我们自己来结盟或摆姿势,以促进大国的地缘战略目标。
在另一个层面上,工人的汇款是另一种形式的食利主义,因为这些收益是在增加国内生产率之外的,其中大部分增加了消费。
房地产行业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尽管它对实际增长的贡献微乎其微。
在塑造民主进程、管理民选政府和边缘化那些被视为对军事统治构成威胁的政府方面,安全国家直接或间接地发挥了关键作用。
67% - 73%的税收来自进口和间接税;个人所得税只占总收入的27%,这表明富人享受的免税待遇与他们获得的巨额收益相比微不足道。
受保护的消费导向是食利者经济的典型特征。投资被转移到产生非生产性租金的领域,如房地产、物业、住房和投机投资。
不充分的土地改革使无地工资和抵债劳工问题得不到解决。由于地主对地方警察、税收和法院、学校、灌溉等国家服务的控制,口袋选区变得根深蒂固。
所有的军事独裁者,涵盖了我们35年的国家生活,扩大和巩固了封建主义,使其成为政治政权的伙伴,在抢椅子的游戏中。
在阿尤布、齐亚和穆沙拉夫的统治下,通过地方政府的实验,将权力下放到基层,目的是为独裁者创造一个选民群体,为他们的统治提供合法性。而不是下放实权,权力更集中于强化封建贵族旨在缩小和削减。
自分治以来,有两个因素对我们所有的国家政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印度的恐惧和对克什米尔的民族统一主义。
我们加入Cento和Seato并不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而是为了在军事上支持我们对抗印度。在独立后的最初几年里,我们被一种恐惧所压倒,害怕作为一个自由国家被一个比我们大五倍的邻国摧毁,这个邻国反对把一个统一的国家分裂成两个。
这导致我们不顾一切地寻求外部帮助,以加强我们的防御能力。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加入了Seato和Cento,表面上是美国领导的遏制苏联领导的“红色威胁”的伙伴,但实际上,我们试图保护自己免受西方对我们生存的任何有害威胁。
国防和军事援助之后,美国、欧洲和布雷顿森林金融机构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财政援助。
据估计,巴基斯坦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了不少于150亿美元的外援,这帮助它成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展示。在齐亚和穆沙拉夫统治的20年里,正是我们在反苏和后来的反恐立场上讨好美国,才使近200亿美元的援助成为表面上的援助,而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
1970年以前的西巴基斯坦和东巴基斯坦关系是一个典型的安全国家和国内食利主义的例子。
在阿尤布、齐亚和穆沙拉夫时期,外部援助提供了350亿美元;韩国在经济形成时期只获得了150亿美元。当外部援助没有用于提高生产率,而是用于食利者保护主义和进口替代时,关键的35年就失去了。
是不是由于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或因素,我们还没有成为一个正常的生产性经济体?安全国家和食利主义在我们的星球上存在吗?为什么一些与我们几乎同时从殖民主义中独立出来的地位相似的经济体表现得更好呢?这些都是需要深刻思考和纠正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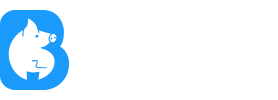













发表评论